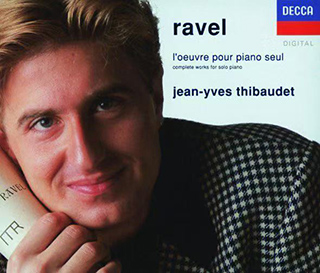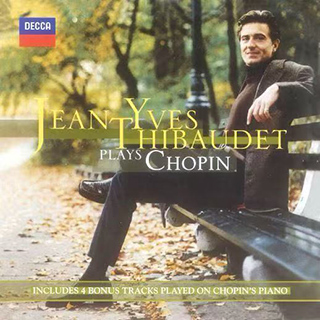上期談及演奏《春之祭》之難,此作對指揮家及樂團同樣要求苛刻,且講求各方高度合作性,彼此稍不協調便會亂作一團。即使世界頂尖樂團要上演《春之祭》,相信也需提前作多番準備,廖國敏與澳門樂團敢於挑戰它,當然別具意義,本地樂迷也應捧場。
筆者感覺整部作品交代得有條不紊,整體結構緊密,各聲部亦呈現有機連繫。由於作品結構複雜,各種樂器、聲部輪替擔當主角,又在多變的節奏中相互交織,現場演奏中出現小瑕疵實在所難免,除此之外,樂團在很多段落都有精彩表現,其中敲擊樂及管樂表現特別優異,可見團員演出賣力,指揮者與整個團隊的事前排練工作也一定不少,他們的努力可說為樂團的演藝水平掀開了新的篇章。
與《春之祭》同場上演曲目為上半場的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第五號鋼琴協奏曲》,這兩部作品同樣誕生於百多年前的巴黎,風格雖截然不同,但放在一起亦挺有意思。有報道指,作為資深作曲家的聖桑出席了《春之祭》的一九一四年巴黎首演禮,但聽不完首樂章便憤然離去,並認為作者是「瘋子」。就此事的真確性,有人求證於斯特拉汶斯基,他表示不存在聖桑拂袖而去的事,因據其所知,聖桑根本沒有出席首演禮。如按斯特拉汶斯基的說法,可能是聖桑明知自己受不了《春之祭》,索性不到,對此作的態度似乎更決絕(一笑)。無論聖桑有否現身,曾處於同一時期的這兩位作曲家,他們的音樂代表了兩種相悖的藝術路向,聖桑接受不了《春之祭》是不難理解的事,他當時如說出:「頂唔順!我走先啦」,已屬較禮貌的回應了(一笑)。
協奏曲主奏者是提博德(Jean-Yves Thibaudet),他是當今法國鋼琴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對聖桑作品可謂駕輕就熟,他的彈奏灑脫從容,造句流暢利落,充分表現樂曲華麗璀璨、玲瓏剔透的美感。奏畢協奏曲後,提博德在返場時表示已闊別澳門樂迷二十一年(我還記得他二零零四年帶來的Debussy作品),很高興能在同一舞台和各位再相聚。
難得鋼琴前的他依然保持瀟灑身段,但見他台風優雅,衣著時尚,顯然很注重台上形象(如不彈琴,他大可當時裝模特),我亦不期然想起另兩位法國鋼琴家Helene Grimaud 和Alexandre Tharaud,他們同樣擁有優雅亮麗的外型,氣質迷人,既是當紅的偶像派人物,又同屬具實力的中青代鋼琴家,欣賞他們的演出,無疑是既賞心悅目加悅耳的事。
提博德加奏了蕭邦的夜曲(Nocturne Op.9 No.2)及拉威爾的《巴望舞曲》(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兩部作品都講求悠揚造句及靈巧觸鍵,以表達曲中輕靈飄逸的美感,他當晚在這方面的刻劃似乎未夠細緻,表現是隨意了點,讓我探究不到樂曲最重要的神髓,尤其《巴望舞曲》中幾個裝飾奏弱音表現差強人意,削弱了樂曲那種柔和而閃爍光芒,可能是鋼琴家旅程勞累所致吧,但半場演出後加奏兩首曲子,也足以令樂迷開懷了。
印象中的提博德一向擅長拉威爾音樂,他最早推出的錄音便是一套拉威爾獨奏作品全集,樂迷如要領略《巴望舞曲》的韻味,最好找這套灌於一九九一年的專輯來欣賞,當中的弱音就是當晚做不到,此現象亦可說是現場演奏之難的另一例子。提博德亦於一九九九年推出一張蕭邦選曲,都是較熱門的獨奏作品,當然包括他當晚加奏的Nocturne Op.9 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