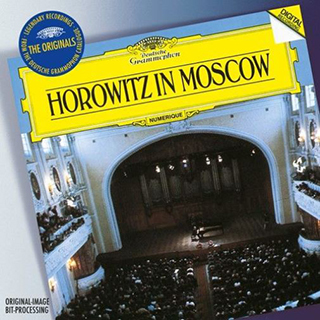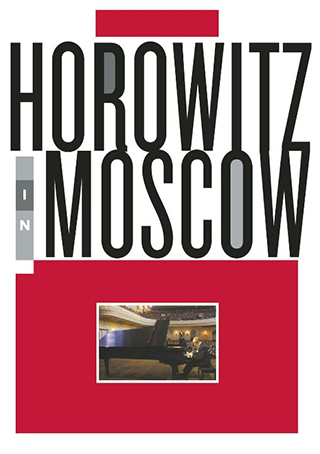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 1903-1989)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分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辦兩場重返祖國音樂會。其中Horowitz in Moscow(霍洛維茲在莫斯科)的錄音及錄像發行後隨即熱賣,也讓樂迷對霍洛維茲的狂熱達至高峰。在這場音樂會中,大師除彈了晚年特別鍾情的莫札特作品及舒曼的《夢幻曲》,亦演奏了史卡拉第、李斯特、舒伯特、蕭邦的樂曲,當然亦少不了俄羅斯作品。
儘管上半場的史卡拉第與莫札特贏來全場喝采,但下半場拉克曼尼諾夫《G大調前奏曲》(op.32 no.5)的音符剛響起,現場氣氛立刻產生轉變。琴音在劇院空間迴響,人的情緒也隨音符的起伏而激盪,透過錄像所見,聽眾或全神貫注於舞台上、或目光凝聚於空間某處、或低頭若有所思,有人已按捺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接下來的拉克曼尼諾夫《升G小調前奏曲》(op.32 no.12)和史克里亞賓的兩首練習曲(op.2 no.1及op.8 no.12),更是霍老施展渾身解數的時候,澎湃音流揮灑出奔放豪情,激昂處教人毛髮直豎,身心都沉浸在無以名狀的興奮中。毫無疑問,很多現場聽眾思緒中的某個共同點被同時觸動了,大師琴音中,除了那股揮之不去的鄉愁,還有把他們連繫在一起的東西,那是共同的家國情懷,此刻,他們比任何時候都要親近。
老實說,筆者每次欣賞此音樂會實錄,都被大師的琴音震懾,也被那現場氣氛感動,可想像當時的樂迷是何等心蕩神馳了。生於烏克蘭的霍洛維茲,離鄉別井大半生後返回祖國,正推心置腹地為同胞們演奏,彷彿在告訴他們:「這才配稱俄羅斯音樂,我沒忘記俄羅斯,也沒忘記你們。」無論何時,霍洛維茲的保留曲目一定少不了俄羅斯作品,那正是他的拿手絕活。
音樂會舉行時,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仍在同一政權下生活,這個大家庭雖然種族複雜,某程度上存在文化差異,但他們大多屬斯拉夫人,說相近的語言,也孕育出風格相近的音樂,人們都習慣統稱他們的音樂為俄羅斯作品。這大家庭中的音樂亦彼此交流,相互影響,例如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首樂章的主題便引用自烏克蘭民謠,此曲更成為去屆奧運會的俄羅斯「臨時國歌」,可見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可惜執筆時,這個曾被他們視為共同家園的地方,早已經歷政治變化而分崩離析,不僅四分五裂,最近還大動干戈,炮火連天。此刻,俄、烏交惡的幕後搞手正發起連串針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竟連帶俄國音樂作品及俄國音樂家也受到牽連,已定及計劃的相關演出一律取消,這是甚麼思維?讓人想起納粹德國禁演曼德爾頌的音樂,實在令人無奈。
筆者無意分析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只是感慨上文的「共同家國情懷」已被完全拋諸腦後,變得毫無意義,因音樂而共同迸發出的真摯激情,今天也蕩然無存。只能說聯繫他們的共鳴紐帶已被撕裂,難以修補了。
霍洛維茲回國演出的動機是純潔的,儘管背後有商業元素,但毫無疑問,他的音樂並無為任何意識形態站台,需知道音樂會前美國剛轟炸了利比亞,引起蘇聯強烈不滿,各地硝煙瀰漫,不同政見對壘陷於白熱化,在當時並不太平的國際形勢下,他的琴音確實超越了政治的藩籬,獲得普世認同。
音樂所能達到的高度,並不在道德層面,但好的音樂最能體現美,這種純粹的美可在最大程度上糅合人類各種情感,讓不同的人產生共鳴,人們如願意一起擁抱這種美,或許會為世界和平帶來希望。今天重溫這場音樂會,實在令人唏噓,除誘發多方面的反思,也教我確信好音樂的永恆價值。◇